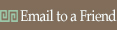一
余英時先生忽然間走了。雖然他年事已高,而且是安詳離世,但事先沒有任何朕兆,大家的驚愕、傷感、難過自不待言,我自己尤其如此,當時情景如今還歷歷在目。8月5日星期四早上我正在吃早點的時候,忽然接到余夫人的電話,說余先生已經睡了好久了,我不解其意,以為是生病,追問之下,這才得她告知:8月1日星期天早上他和我通話,此後12點左右,也就是美國東岸時間星期六的午夜,他還和金耀基兄通電話,然後去睡覺,夢裏過了,再沒有起來,此時已經入土為安。當時聽了余夫人這些話,真是驚駭莫名,所謂世事無常,人生如夢的滋味,都一起湧到心頭。即使到了今天,英時兄已經走入歷史,再也不會如常和我們談笑,為廣大讀者論述歷史這個事實,仍然好像十分虛幻。
我和英時兄相識超過一個甲子,算是很有緣分,一見如故,但其實除了短短幾年的相處之外, 一直遠隔重洋,音訊稀疏。只是到了最近幾年電訊方便,這才有機會經常聊天。7月中他來電話, 告訴我他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英譯本出版了,並且已經用快遞分別寄給我和金耀基兄留念。果然,這書在7月29日就寄到,第二天星期五我打電話去致謝,他不方便接,我們約定星期天早上再通話。到時他一早倒先打過來了,顯得很高興,但語調卻比往常更為低沉,而且不斷慨嘆時局,我除了多謝贈書和懇請多加保重之外,也想不到別的話來為他開解,只好怏怏掛斷, 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就是訣別了!現在回想,最近大半年以來,他大概自覺日漸疲乏,已經多少有些預感,所以經常提到已經累了,再沒有興致寫作,以及老朋友難得,彼此保持健康最為重要之類的話。很遺憾,我一直沒有留意這些徵兆,失去了和他深談的最後機會。
二
英時先生名滿天下,但大半生是在大洋彼岸度過,做事、成家、成名、得獎都是在美國。然而,他的根、他的心,他最重要的影響,卻是在中國,特別是在台灣和香港。這一點本校的,特別是新亞書院的許多同事大概都知道,但也不一定很清楚。現在容許我用一點時間把他和香港以及中國的幾層關係稍為講一下。
英時兄夙慧好學,但童年和少年時期正當八年抗戰,被迫在閉塞的安徽老家度過,他的青年時代碰上國共內戰,又飽受時局動盪之苦,都不利於才學的發展。他在1950年也就是二十歲的時候從燕京大學到香港來探親,然後戲劇性地決定在香港留下,那是個重要轉機,隨後那五年,就成為他一生的關鍵。首先,這是他在成年之後,初次得享家庭溫暖,在雖然艱苦但相當穩定的環境中成長。其次,他父親和錢賓四(錢穆)先生相熟,因此不久之後他就進了新亞書院,成為這位當代大儒最器重的入室弟子,那在師生兩方面都是難得的緣分。這奠定了他學問的基礎,也決定了他的人生路向。第三,同樣重要,但不太為人注意的,則是他在勤奮治學之餘,還有無窮精力去涉獵大量西方歷史、社會學、政治學著作,同時探索新思想、寫文章、出書、辦報、編雜誌、搞出版社,成為非常活躍的年輕文化人。當時他和友聯出版社以及《中國學生周報》、《民主評論》、《自由中國》、《人生》、《祖國周刊》等五六份刊物都有密切關係,更曾經創辦高原出版社和《海瀾》雜誌。
換而言之,他日後的兩個世界,正就是在這五年之間建立起來:中國歷史研究的世界是在新亞書院錢夫子的循循善誘之下形成;當代中國批判的世界則是通過自發學習,以及和他所謂「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匯聚而成的社群」相互碰撞、激發而形成。前者是學術性、思辨性的,後者是社會性、活動性的。前者成就了他的事業和名望,後者成為他中國情懷的寄託,從而賦予他生命另一個向度,另一層意義。這兩個世界迥然不同,卻是互補而又互相促進的。
三
在1955年到了劍橋之後,英時兄的事業可謂一帆風順,一往無前,此後碰到的唯一挫折,便是1973至75年回到中文大學擔任新亞書院校長那一段經歷了。當時由於主持負責大學改制的工作小組,他飽受攻擊和非議,心理大受創傷,從此堅定了回到美國發展的決心。這在當時是哄動社會的大事,看來好像非常之不幸,其實並不盡然,我們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大學而言,改制是三所成員書院集中到馬料水新校園之後,協同發展所必須,阻力雖大也無可避免。就新亞書院而言,改制誠然非常痛苦,但也有意想不到的後果,那就是機緣巧合,找到了一位兼具政治智慧與槃槃大才的「局外人」來出任改制之後的新院長。他不但在相當程度上平息了由改制所造成的紛爭,而且創辦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更把自1964年以來就已經黯然離開新亞的錢先生從台灣請回來主持首屆講座,使得新亞書院和它的創始人之間能夠重新建立密切和長遠關係。當然,大家都知道,這位令新亞書院脫胎換骨,以嶄新精神面貌重新出發的新院長就是今天在座的金耀基校長。最後,對於英時先生本人而言,我們現在知道,當年李卓敏校長接受了他得意門生邢慕寰教授的策劃,的確有意以英時先生為接班人;港督麥理浩更曾在私人晚宴中當面表示, 希望他能夠擔起這重任。然而,英時兄本人顯然更愛好寧靜的研究和教學生涯,而憚於繁複的行政工作和人事關係,所以對他而言,回到美國東岸的常春藤盟校發展比之領導新成立的中文大學其實是適合得多。工作小組事件在無形之中為他做了這個艱難的決定,同時更消解了他當年學成之後返回新亞書院任教的承諾。所以,整體看來,此事對他也可謂焉知非福了。2007年新亞書院和崇基學院共同創辦「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2009年中大哲學系校友捐款,為當年反對新亞改制最激烈的唐君毅先生在校園內豎立銅像,英時兄應邀以門人身份為此像撰寫銘文。這樣,經過了數十載光陰,他和新亞元老之間的裂痕也終於彌合了。
四
英時先生是新亞書院最傑出的校友,也是錢賓四先生最得意的門生,他們師徒二位都將畢生奉獻給中國歷史研究,最後又不約而同,都被吸引到相同的兩個歷史題材上去,相信這並非巧合, 而是反映他們對於中國文化傳統重心的判斷。如所周知,賓四先生晚年以極大宏願,完成了他的五卷《朱子新學案》,而英時先生的壓軸之作,則是同樣龐大的兩卷本《朱熹的歷史世界》。這兩部著作都以朱熹為中心,然而重點、觀念、格調卻全然不同。其次,賓四先生最後的作品是「論天人合一」那篇短文,英時先生的收官之作則是《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這兩者的規模和精神也迥然相異。我想,這些學術上的異同,就正好象徵了過去大半個世紀中國史學的變和不變吧。今後我們站在「天人合一亭」遠眺八仙嶺和吐露港的山光水色之際,也許都會想起在新亞源頭的這兩位學者,甚至覺得,他們好像已經回到新亞書院來了。當然,他們根本就是新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應該說從來就不曾離開過吧!
2021年10月27日於用廬
(本文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余英時教授追思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