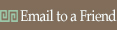畫琺瑯是於十七世紀末從歐洲傳入中國的技術和舶來工藝品,中國積極學習後,從十八世紀開始反成為盛行於海內外的新潮流產品,不僅深受國內市場青睞,同時外銷各地而廣受歐洲及其他各國歡迎。彼時廣東和北京宮廷是金屬胎畫琺瑯的兩大製作重鎮,後者即是宮廷作坊而只為皇帝一人的需求服務;而前者則是生產應市場需求之商品,所以造型和圖案裝飾都萬象森羅,甚至千奇百怪,以求滿足和吸引各方客戶,因此也創造出許多特色產品,使廣東金屬胎畫琺瑯以「廣琺瑯」之名為人所知。廣琺瑯的最大外銷市場以歐洲為首,顧及西方客戶的需求,加以廣州為當時中國與歐洲往來的首要交通樞紐,容易取得各類西洋圖像,它們自然成為廣琺瑯上的主要紋飾之一,並加入了廣東畫琺瑯人的創意改造。這些西洋裝飾不只擄獲西方市場,也為中國人所喜。近期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總相宜:清代廣東金屬胎畫琺瑯特展」及其與深圳博物館合辦的「渾融中西.絢彩華麗:清代廣東金屬胎畫琺瑯特展」,便搜集繪有各類西洋圖飾的作品,揭露其受寵市場之緣由。
一、廣東畫琺瑯人的文創
廣琺瑯上的西洋圖像以西洋人物圖為主流,或因人物是最容易表現異國風情特徵的對象,故中國的畫琺瑯人多選擇以他們作為代表西洋元素之裝飾。如開光西洋人物方杯(圖1),其四面各有一個方形開光,除了把手面的開光內畫中國花草外(圖1–a),其餘三面的開光都畫有半身的西洋人物(圖1–b、圖1–c)。他們都置身在中式戶外空間,這種西洋人物搭配中國背景的圖像是廣琺瑯中常見的組合。另一件作品錦地開光西洋人物圖蓋碗更是明顯帶有這種特徵(圖2),西洋人物皆處於中國園林或山水中。想當時中國場景的背景圖像相當受西方市場所青睞,在不少訂製的廣琺瑯外銷紋章器物多見中國山水、園林庭院、亭台樓宇或山石花鳥等作為裝飾,如廣東省博物館所藏的銅胎畫琺瑯庭院嬰戲圖紋章花口盤(圖3),盤中心畫着可能是英國西薩塞克斯郡(West Sussex)的Yaldwyn family的家族徽章,1 然背景則是中國庭院人物圖,盤口邊沿也是中國花果的裝飾。
這類在中國特色空間中的西洋人物往往形貌奇特、似中又西,是廣東畫琺瑯人所形塑的公式化結果,即以中國傳統人物畫之線條筆法描繪簡化後的西洋人物。方杯和蓋碗上的西洋人都以高挺的鼻子和深邃的雙眼皮來表現其五官立體的特徵,男士和女子則各以妝髮和衣飾來區辨。西洋男士基本上都是及肩的棕色長捲髮,或頭戴黑色三角帽(tricorn),上半身穿着由白襯衣、長外套和領巾組成的服飾套件;下半身(以蓋碗上的圖飾來看)多是及膝的短褲、長筒襪和黑鞋。這樣的服裝款式大致符合歐洲十七世紀中期開始流行至十八世紀末的紳士服飾,2 也幾乎是所有廣琺瑯上西洋男士的裝扮,並不時會在其腰部覆上一條披巾,想該是中國畫琺瑯人的創意。至於當時歐洲女性的裝扮比男裝要來得多樣且花俏,但廣東畫琺瑯人仍歸納出一些基本的元素。西洋女性人物的頭髮多向上梳起,身穿領口低垂的荷葉邊U型領襯衣、外罩長裙、袖口露出襯衣的褶飾(engageantes),這是流行於十八和十九世紀歐洲的女裝花邊袖子;且她們同廣琺瑯中的男性一般身上多配有披巾。
這種公式化的西洋人物造型,加上中國繪畫性的線條表現,使得它們看起來不僅與實際的歐洲人樣貌和妝容相去甚遠,也顯得滑稽古怪,不少情況甚至看似中國人裝扮成西洋人的角色扮演(圖4)。有論者認為這是中國畫琺瑯人不諳西洋人物形貌和歐洲繪畫技法之故,3 又或是尚在學習、發展的初期作品,所以才會有這般奇形怪貌。此說看似合理,但細想卻頗多破綻。首先,繪製這類西洋人物圖飾的廣琺瑯數量相當多,且製作時期貫穿整個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這顯示它們是有一定「人氣」的流行圖案,畢竟廣琺瑯是以販售為目的而製作的商品,若果是粗陋的圖繪,又怎會風行且持續大量製作?而且這樣以中國筆法描繪西洋人物的情況同時出現在當時的外銷瓷上,像是乾隆時期(1736–1795)一對西洋人物琺瑯彩瓷碟亦呈現如同卡通人物般的有趣奇特形象(圖5),然其圖像內容是有所本的,以意大利巴洛克畫家阿爾巴尼(Francesco Albani, 1578–1660)的《四元素》(Allegoria dell'elemento)組圖中的〈火〉(Allegoria dell'elemento del Fuoco)為參照來繪製,該組圖的四幅大畫在十八世紀多次被轉作版畫廣泛流傳(圖6),也來到中國成為外銷瓷器上的圖飾。
二、廣東畫琺瑯人的出眾畫技
這便涉及另一個問題,即認為中國畫琺瑯人不善捕捉歐洲人的形貌和不諳西洋繪畫或畫琺瑯技法,所以即便如該件外銷瓷碟在有歐洲版畫作為參照圖稿之情況下,中國畫琺瑯人仍畫出如此詼諧的西洋人物。然而這種說法也不甚合理,除了商業考量下不會容許圖繪不佳的拙劣商品被持續地產出,中國和廣東畫琺瑯人的繪畫技藝實際上相當好,因為畫琺瑯的釉彩特性能夠表現筆墨線條和渲染層次等細緻的效果,使繪畫或中國書法等講究筆觸的藝術形式得以原樣移植到器物表面上(圖7),呈現的水準幾可媲美紙本或絹本繪畫,所以畫琺瑯人多應具畫家根底、備一定的繪畫功力及專業技巧。因此在記錄清宮各工藝作坊活動的《活計檔》中,常可見當琺瑯作閒暇時,畫琺瑯人經常被調派至協助宮廷繪畫的製作,如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的〈記事錄〉載:「初六日,催總鄧八格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琺瑯處畫琺瑯南匠九名現今無差,著鄧八格撥幾名幫金昆畫木蘭圖、蠶壇圖,欽此。」4而乾隆六年(1741)後宮廷中的畫琺瑯南匠多是徵召自廣東,可印證廣東畫琺瑯人的畫技高超,備具能力參與宮廷繪畫之製作。他們甚至可以獨立承做繪畫的差事,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近年關時,〈琺瑯作〉的檔案便有記載畫琺瑯人被交辦繪製年畫和歲軸對等年節字畫:「初二日,副催長吉文來說,太監如意交年畫尺寸帖一件、綠絹歲軸對一副。傳旨,著交琺瑯處畫琺瑯匠黎明畫年畫一張、歲軸對一副,欽此。」5 根據《活計檔》的記錄,這位畫琺瑯匠黎明(生卒年不詳)亦來自廣東,於乾隆三十八(1773)為當時的粵海關監督德魁(生卒年不詳)舉薦入宮服務,6 北京故宮博物院現仍藏有黎明所繪的《仿金廷標孝經圖》冊等宮廷繪畫(圖8)。
見諸廣東畫琺瑯人的畫功優秀,加上歐洲畫琺瑯這種可以表現細緻繪畫效果之新材料與技術,理應盡可發揮及強化他們表現描繪物象的技巧,為何卻將這些西洋人物描繪得如此奇異?個人認為這是廣東畫琺瑯人之選擇的一種創作表現,而選擇以中國筆法處理西洋人物或基於效率的考量。廣琺瑯既是商品,自當以利益為優先追求一定的製作效能,因此除了將西洋人物的造型公式化使繪製簡捷外,再以中國繪畫中最基本且重要的線條、也是中國畫家所嫻熟的技法來描繪自是較為得心應手。這般手法不僅得以提高產能,更讓即使未見過歐洲人的中國畫家也容易熟悉上手,畫出有趣的西洋人物。
此外, 這種繪製模式與當時中國工藝作坊高度分工以兼顧產量和品質的情況相當吻合。以景德鎮的製瓷工序為例,法國耶穌會士殷弘緒(Père 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在1712年9月1日寫給巴黎耶穌會中國和遠東傳道團教務代理奧里(Louis-François Orry, 1671–1726)神父的信中,7 詳述了他在景德鎮所見的瓷器上彩方式:「繪畫工作是由許多畫工在同一工場裏分工完成的。一個畫工只負責在瓷器邊緣塗上人們可看到的第一個彩色的圖,另一個畫上花卉,第三個上顏色,有的專畫山水,有的專畫鳥和其他動物。」8 可見光是「畫胚」的繪瓷階段就是由一組畫工來共同合作,分別由善畫山水、花卉、鳥獸、人物等不同匠人來完成,所以在許多介紹中國製瓷過程的外銷畫冊中,都可以看到多位畫工各司其職的流水線繪製模式(圖9)。廣琺瑯的製作基本上應也大同小異,所以那些奇特的西洋人物該是商業化生產下的一種創作風格,而非中國畫琺瑯人無法掌握歐洲人樣貌的緣故。
三、兼通西洋技法
至於西洋繪畫或畫琺瑯技法,廣東畫琺瑯人其實也甚為熟悉並掌握得相當好,有傳為廣東畫琺瑯人林朝楷(活動於十八世紀早期)所畫的《牡丹圖》大軸為例(圖10),其以西洋明暗和色彩對比的技法寫實描繪牡丹和其木盆上的紋理。林朝楷於康熙(1662–1722)晚年入宮服務,並習畫於鼎鼎大名的清宮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9 此畫確屬郎氏風格,但是否真如其落款所言「摹郎世寧畫本,臣林朝楷恭畫」(圖10–a),仍需細緻的研究。此外,不少廣琺瑯的西洋圖飾是採用西洋手法來繪製的,例如十八世紀中期一個西洋人物圖蓋碗的碗身有三個開光紋飾(圖11),各畫一歐洲神話場景,其中一景也重複在碗托的開光紋飾內(圖11–a),看來是該組器的主紋。這些圖飾都採用歐洲的點描法(pointillé)來描繪,以細緻的小點來處理物象的明暗和表現人物五官及肌理的質感。此技法來自流行於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袖珍畫琺瑯肖像(圖12),10 這種袖珍畫琺瑯片也常被歐洲商人和傳教士等帶到中國銷售或送禮,廣東畫琺瑯人或由此習到此技法,且歐洲畫琺瑯技法中似以這種點描法或點畫法較容易學習和模仿,11 故廣東畫琺瑯人可能因此選擇這種畫法來繪製西洋風格的圖飾。
雖然這些圖飾所根據的圖像來源仍未明朗,但基於它們重複出現在不同的廣琺瑯器上(圖13),甚至是琺瑯彩瓷上(圖14),想見有歐洲圖稿在廣東流傳作為圖飾的參照。另外,即便它們的圖像來源尚不明,但從其圖像元素已可辨識出主題內容:坐在兩輪座車的女性人物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大地女神西布莉(Cybele),三位女性人物的場景分別是穀物花果三女神席瑞斯(Ceres)、芙蘿拉(Flora)和波摩納(Pomona),另外一景則可能是描寫自然之神維爾圖努斯(Vertumnus)向果樹女神波摩納求愛。開光外的紋飾亦搭配西洋卷草紋,其中心的主要花卉可能是銀蓮花、鐵線蓮等西洋花卉紋,圈足處則裝飾包含葡萄、番石榴、鳳梨等各種水果的果實紋飾。這些紋飾可能也有歐洲範本,並指定搭配這組人物圖像。這些女神都是植物、花果等自然物產的掌管者,尤其大地女神西布莉更是主宰萬物的生產,所以在十六到十八世紀的歐洲繪畫中,她經常伴隨各種蔬果、作物和花卉等元素出現。像是哈布斯堡布拉班特公國(橫跨現今部分的荷蘭、比利時和法國)的著名畫家勃魯蓋爾(Jan Brueghel the Elder, 1568–1625)所畫的Garland of Fruit Surrounding a Depiction of Cybele Receiving Gifts from Personifications of the Four Seasons(1620–1622),這是一幅以西布莉為主題的大型裝飾花環畫,12 花環框架中描繪西布莉接受四季的化身人物的獻禮,花環邊飾則是由各種鮮花和蔬果所組成,象徵對女神的致敬和歌頌她所帶來的豐饒物產。
四、潮流圖飾的廣大市場
不論是中國風格或西洋技法的西洋人物圖飾都受到西方市場的欣賞,再回顧本文開頭談到的那件裝飾奇特西洋人物圖的單把小方杯,與現代濃縮咖啡杯的大小相當,方杯和杯把都是中國少見的杯式及造型,但頗見於廣琺瑯中,應是當時外銷歐洲所做。這種杯式稱為“demitasse”,意為小咖啡杯,在當時主要用作飲用濃縮咖啡、卡布奇諾或土耳其咖啡等濃厚口味的咖啡。這種小杯或其他類型的咖啡杯、茶杯,通常都配有相應的托碟,且托碟的深度較現代者更深,此與當時歐洲上層社會飲用咖啡和茶的一種有趣方式有關——不是用杯就口喝,而是用其所配的托碟來喝。因為杯中的熱飲太燙,便將其倒入碟內降溫,然後直接就碟飲用(圖15)。這樣的咖啡和茶的飲用方式也被帶到歐洲國家的殖民地,美國剛成立時就國會結構該為一院或兩院制面臨爭論,傳聞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和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就此有一段以飲用咖啡做為譬喻的著名對話。華盛頓主張採參、眾兩院制而傑佛遜則認為參議院純屬多餘,所以華盛頓趁着一起喝咖啡時問傑佛遜:「你為何要將咖啡倒入碟中?」後者回答:「為了冷卻咖啡啊。」華盛頓便說:「正是如此,我們應將〔眾議院的〕法案倒入參議院的碟子中冷卻一下!」13 雖然不確定這段對話是否真實發生或為軼聞,但透露了當時西方社會以碟飲用咖啡的習慣。直至今日的北歐地區和新加坡,不少年長者依然保持用碟而非用杯來喝咖啡的方式。而廣琺瑯杯因為金屬胎體易導熱,人們可能也會將熱飲倒至其碟中冷卻後飲用。
此外,西洋圖飾並非只為外銷品而做,其在中國本地也有相當的市場。《紅樓夢》第五十二回寫賈寶玉的大丫鬟之一晴雯病了,寶玉便讓另一大丫鬟麝月取來鼻煙來舒緩其頭痛、鼻塞的症狀:「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的小扁盒兒來,遞給寶玉。寶玉便揭開盒蓋,裏面有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趐,裏面盛些真正上等的洋煙。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嗅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14 這裏的西洋琺瑯可能是歐洲進口的舶來品,亦可能是廣東所做的西洋款式琺瑯,不論何者都顯示西洋人物圖為中國市場所喜。所以廣琺瑯中有許多裝飾着西洋人物的中國用品,如鼻煙壺(圖16)、手爐(圖17)和渣斗(圖18)等。綜言之,廣東畫琺瑯人的創造力卓越,他們善於吸收各種圖像、造型和技法,經其融合和活用,並結合自身熟悉的中國繪畫圖式、元素和手法,創作出不論對海外還是國內市場都深具異國風格的圖飾。西洋圖像可說是廣琺瑯的圖像中最具創意和表現力之處,中國畫琺瑯人各以其理解來詮釋這些外國人物和活動,藉以吸引着中外市場。
注釋
1 David S. Howard, Chinese Armorial Porcelain(London: Faber & Faber, 1974), p. 235.
2 John Peacock, The Chronicle of Western Costume: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o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1), pp. 115–152.
3 W. L. Hildburgh, “Chinese Painted Enamels with European Subjects,”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79, no. 462(1941), p. 84.
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205。
5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9,頁821。
6 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記事錄〉載:「十八日,造辦處謹奏,為請旨事前因牙匠李爵祿呈請終養、琺瑯匠黃國茂手藝遲慢又兼有疾,俱經奏明令回原籍,著該關另選好手牙匠一名、畫琺瑯匠一名送京補替應役等因在案。今據粵海關監督德魁選德牙匠楊有慶、畫琺瑯匠黎明二名前來,奴才等隨試看得伊等手藝尚堪應役。」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6,頁651。
7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將這封信的標題譯為〈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神父致耶穌會中國和印度傳教會巡閱使奧里神父的信〉,但法文原文稱奧里神父的身份為“procureur des mission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英文該為“Procurator of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and the Indies”,當時“Indies”並非僅只印度,而是包括印度在內的遠東地區;且據劉國鵬的考證,“procurator”一詞應稱為「教務代理」,故本文將奧里神父的職稱表述為「耶穌會中國和遠東傳道團教務代理」。參劉國鵬:〈梵蒂岡原傳信部歷史檔案館所藏1622–1938年間有關中國天主教會文獻索引鈎沉〉,《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5期,頁100–113;關於英文譯稱,參Howell G. M. Edwards, Nantgarw and Swansea Porcelain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Dordrecht: Springer Nature, 2018), p. 2。
8 杜赫德(Du Halde)編,鄭德弟譯:《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中國回憶錄Ⅱ》(鄭州:大象出版社,2001),頁98。
9 雍正六年(1728)七月,〈雜錄〉載:「十一日,員外郎唐英啟稱,怡親王為郎世寧徒弟林朝楷身有勞病,已遞過呈子數次,求回廣調養,俟病好時再來京當差。」由此得知郎世寧和林朝楷的師徒關係。參《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頁423。
10 Cyril Davenport, “Portrait Enamels,”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 56, no. 2891(1908), pp. 573–580.
11 Cyril Davenport, “Portrait Enamels,"p. 574.
12 Anne T. Woollett and Ariane van Suchtelen eds., Rubens & Brueghel: A Working Friendship(Los Angeles: J. Paul Getty Museum, 2006), pp. 156–165.
13 Max Farrand e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 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359.
14 曹雪芹:《紅樓夢》(上海:世界書局,1934),第五十二回,頁326。
|